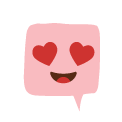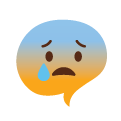兒女為我慶祝六十歲生日之後的第二天,我和老伴一起搭乘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倫敦,然後轉飛維也納。希斯羅機場保安甚嚴,過境乘客也必須接受繁複的檢查,幸好下個航班在三個小時後才起飛。幾經周折,終於通過關檢,才不致誤了航班。
黃健兄的嫂夫人Cecilia親自前往機場接機,她說旅遊旺季已過,由機場通往市區的公共交通很暢順,比計程車的收費低很多,建議我們和她一起搭乘。盛情難卻,我們跟著她這樣做。
維也納機場給我的印象是,規模比較其他國際大都會的機場小,設備也比不上那般現代化。由機場往市區走,經過一座巨大的煉油廠及一家發電廠,附近有很多廉價的屋村,大概是工人的住宅吧!沿途都沒有什麼耀眼的設施,與維也納的國際形象不匹配。
黃健是多倫多好友露露的弟弟,他們夫婦很客氣,將女兒暫時空出的單元作為我們臨時的居所。他們住在同一建築物內的另一單元,方便照顧我們。他們唯一的女兒Valentina去了台灣,修讀中國文學。她本來修讀法律,只差一年便完成博士課程。華人的子女一般都很進取,在學術及專業領域上出類拔萃。黃健夫婦對女兒的抱負與成就感到驕傲,這是人之常情。
黃健夫婦在三十年前從香港移民奧地利,經過艱苦的掙扎,終於立穩了腳。黃健仍未退休,在尼日利亞大使館擔任要職;妻子退休後,投身社會,擔任義工,為華人社區及教會服務。他們已精通本地的語言,同時已適應這裡的生活。從香港移民維也納的家庭寥寥可數,從中國大陸及台灣來的便比較多,而且還陸續會來。黃健夫婦已習慣了維也納的生活方式,非常投入,他們將會終老於此。
我們在維也納逗留了五天,幾乎走遍所有博物館。走累了,到處都有咖啡座,買杯香味撲鼻的咖啡,挑件甜點,歇一會,體力回復後又可再逛。黃健白天上班,任由我們自由活動,他認為這裡治安比較好,只需提防扒手便可。我們購買了兩張一週有效的交通系統套票,每張12.5歐羅,不限次數在市區範圍內可搭乘巴士、電車及地鐵,既廉價又方便。
維也納人在公眾地方不喜歡提高嗓門講話,地鐵乘客,餐廳食客,都是靜靜的坐在一角,交談時都調低了聲量,不像中國人那樣誇張,不怕妨礙他人。維也納人也講究衣著,在不同場合穿起不同的衣服。我們到人民歌劇院(Volksoper)觀賞歌劇那晚,黃健借出他的西裝,並提議我一定要穿起才好進場。假設我没有照着做,那次肯定會尷尬得無地自容。
北美洲指定公眾地方不准吸煙,已實行多年,違者會受到警告或罰款。但這項禁令在歐洲便難以嚴厲執行,餐廳都不設禁煙區。我最初不留意,後來才發覺,便也入鄉隨俗。
來到維也納舉目可見都是莫札特的標誌,介紹他的出生地、故居及他的生前事蹟。商人借助他的名氣,匪夷所思,將商品命名為「莫札特巧克力」、「莫札特旅社」......在黃健不用上班那天,他帶領我們到維也納公墓憑弔一些偉人。我們發現了貝多芬及舒伯特的墓地,在他們墓穴旁邊也發現莫札特的墳墓,但聽說他的遺體不在這裡,也不知埋葬在何處。莫札特生前曾經風光一時,但死後遭人遺棄,令人聽了傷心不已。
維也納除了大型的歌劇院與音樂廳之外,到處都有專為遊客演出音樂的場所,每晩都有莫札特作品的演出。街頭的「黃牛黨」,將自己化妝成莫札特的模樣,拿著戲票抬高票價向遊客兜售。莫札特在天之靈,對此不知會有什麼想法呢?
奧地利東面的鄰國有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蘇聯解體前,中國人都不需簽證便可自由進出這三個東歐國家。很多中國人到了東歐之後,便伺機越過奧地利邊境,前往西歐國家,並企圖留下來,成為非法移民。奥地利的自由黨一直設法堵塞這個漏洞,對所有從東歐偷渡過來的移民都不歡迎。在維也納我們曾經受到一些本地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或許誤認我們便是那類不受歡迎的移民。
維也納只有屈指可數的移民家庭是從香港來的,其他都是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家庭。他們很多經營餐館,洗衣店早已無利可圖而關閉。黃健的妹夫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開餐館,專為華人旅行團服務,生意非常好。付出的代價是每週七天,每天十多個小時都不能離開工作崗位。我相信只有吃得起苦的人才可幹這門生意。
奧地利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我們告別黃健夫婦之後,租用了一部小汽車作「自駕遊」。我們朝着薩爾茨堡(Salzburg)的方向走,一出高速公路便提心吊膽,因為奥國人開車都不理限速的標誌,風馳電掣,不停超前,為了安全起見,我只有避開。按照規定的時速,在公路上走了大約一個小時,梅爾克修道院(Melk Abbey)便出現在視線內,這是建在山頂上的一偉大建築,居高臨下,俯瞰在下面穿過的多瑙河。我找個位置將汽車泊好,參加了一個有專人講解的遊園隊伍,暢遊修道院內的設施與僧侶們生活及學習的場所。離開修道院之後,我們往山下走,來到一家古色古香的小旅社,並決在此逗留一夜,享受無拘無束的二人世界。
奧地利的版圖不大,到什麼地方去都很方便,不需趕路。在梅爾克修道院的山腳下度過了一個寧靜的晚上,又準備上路,往薩爾茨堡去。走上高速公路之後,突然霧氣從遠處飄來,而且愈來愈密,遮蓋了整個環境。我全神貫注,穩握駕駛盤,降低車速,與前後的汽車保持安全的距離。車龍開始形成,愈來愈長,見首不見尾。我聽到警笛聲,由遠而近,由疏變密,聲音刺耳,知道前面已發生了交通意外。果真如此,高速公路很快被堵塞得針也插不進。我想與其被困車內,不如設法將汽車移到路旁停下,找個地方歇腳,等到路面情況好轉後才再動身。
起程前黃健鄭重推薦奧國風景宜人的湖區(Ausseerland-Salzkammergut),尤其不能錯過著名的阿特湖(Attersee),並在地圖上做了記號。按照他的指示,我們不費工夫便找到這個似曾相識的地方。原來不少旅遊指南的頁面都有圖文並茂介紹過這個美麗的湖畔小鎮,所以對它不感陌生。鎮內有很多B & B家居式的小型旅館,因為旅遊旺季已過,我們有很多的選擇,只是眼花撩亂。最後決定在靠湖的一家過夜,並連忙打電話給黃健報平安。從晚上的電視新聞報導獲悉,當天的交通意外造成七人死亡,受傷人數更多。
我們開車沿著黃健推薦的湖區漫無目的地轉來轉去,由一個景點走到另一個景點。湖光山色,各有千秋,目不暇給。既然如此,我們選擇在沃爾夫岡湖(wolfgangsee)的湖畔名叫聖吉爾根的小鎮(St. gilgen)停下。飽嘗風景之餘,還享受了一頓美味可口的湖鮮餐。無論到那一個地方我們都不願意離開,恨不得能夠長居於此,與大自然共老。
記憶所及,我們到過Stobl,St. Wolfgang,Bad Ischl,並最後在哈爾施塔特(Hallstatt)的湖畔小鎮留下。這裡很早便有人居往,我們投宿的小旅館便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小鎮背山而建,山高二千一百公尺,山頂整年積雪,我們搭乘纜車上去,俯瞰山下的湖泊,遥望阿爾卑斯山脈的群山。這個地方,冬天是愛好滑雪運動者的天堂,夏天是愛好爬山人士的聖地。我們參觀了在半山腰的天然冰洞,據說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
一整天的體力活動使我們開始感覺疲累,不假思索便停留在奧爾陶斯(Altausee)休息。它名氣雖然比不上附近的小鎮,但没有令我們失望。奧地利的湖區都是風景如畫,猶如人間仙境。
中秋過後,天氣轉涼,霧大有雨,再不宜在湖區久留,我們決定重新上路,往薩爾茨堡的方向走。雨繼續下,雖然行車不方便,但毛毛細雨下的薩爾茨堡卻有另一番風韻,增加了它的魅力。維也納被公認為奧地利的皇冠,薩爾茨堡便是皇冠上的明珠,光彩照人。一進城,便聞仙樂處處飄揚。到底是好萊塢的音樂劇使薩爾茨堡名震遐邇,還是片商巧妙利用薩爾茨堡之名去推銷電影呢?姑且勿論怎樣,薩爾茨堡確是名不虛傳的音樂聖地,莫札特曾以此為家。我們來到那天便購票進場,欣賞在莫札特故居演出他的作品。著名指揮家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也曾以此為家,肯定了薩爾茨堡的特殊地位。
薩爾茨堡像是一座大型的音樂廳,充滿節日的氣氛。無論走到那裡,都聞音樂聲,如影隨形。星期天到處有不同的戸外表演,水平極高,吸引不少途人圍觀。我們來到的第二天,欣賞了一場在天主教堂內舉行的音樂會,由當地一個青少年樂隊演出,都是免費的。此行最大收獲是觀賞了一場超水準的現代舞,背景音樂是法國作曲家拉威爾(J M Ravel)的Bolero舞曲,極盡視聽之享受。
離開薩爾茨堡之後,我們朝著因斯布魯的方向走,穿越阿爾卑斯山遼闊的山谷,經過很多村莊和小鎮:Bad Reichen Hall,Lofer,St. Johann及Worgel。雨繼續下個不停,但沒有影響我們旅遊的熱忱。沿途風景實在太吸引人,可惜只能走馬看花。
我們中午到了目的地因斯布魯,Maria和丈夫David開了一輛保時捷(Porsche)跑車來酒店接我們。Maria是黃健的妹妹,雖然第一次見面,但都對我們很熱情。他們二十五年前從香港移民奧地利,先以維也納為家,後來才遷到這個城市,開設中餐館,經營得法,有利可圖。在外國目睹事業有成的朋友,會分外感到安慰。
因斯布魯是1976年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因此名噪一時,使餐飲業受惠。David和Maria看準時機投資,值得一讚。工餘時間,David喜歡搜集Swarovski 的水晶製品,在家中展示。我們被邀請參觀,大飽眼福。他也帶領我們到水晶製造廠實地觀察,增廣見聞。某天雲淡風輕,他開車帶我們登山,參觀跳台滑雪的跑道,我有畏高症,感覺高處不勝寒。這項運動除了需要難度極高的技巧之外,還需過人的膽量。對膽小的人來說,這項運動是絕對不適合他們的。
我們奧地利之旅,便在因斯布魯圓滿結束。
原圖: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