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法院審理具政治色彩的案件數目比以往多出幾倍,案情的暴力成份也愈趨嚴重。筆者雖至今仍認為法庭於原則上不容忍暴力,但在這數月間,不知是法官是否對政治暴力「司空見慣」,在刑罰上甚至判理上,竟似有麻木、降低底線的情況出現。早前終審法院當庭釋放東北暴徒,已令筆者頗為困惑,現在黃毓民「掟」玻璃杯一案中,法庭所頒判詞,更使筆者大惑不解。黃氏一案令筆者不禁質疑,法庭是否欲為持續暴力開出先例?甚至乎,在如此明目張膽的暴力行為中,增加受害者的舉證責任,迫使市民不可再依靠法庭的判斷?
高院判案理由 令人費解
讓我們先了解本案判詞。法庭指,在審理這宗案件時,重點分為兩個層次:梁振英有否因「掟」水杯行為「感到震驚」及黃毓民的有否持「襲擊」目的。在刑事法上,犯罪行為(Actus Reus)及犯罪意圖(Mens Rea)需同時出現,才能作出「犯罪」的判決,因此在這方面,法庭把梁振英的反應和黃毓民的行為放在一起看,筆者可以理解。
然而,筆者則對法庭在推斷以上兩者的理由抱有極大懷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指,原審法官並無充分考慮閉路電視的片段,以及黃毓民的議員身份、他以往相類似的行徑、水杯被拋出的方向、着地點,裁定控方未能舉證證明黃毓民的犯罪行為和意圖。
可是,若對原審裁判官的判辭加以研判,不難發現上述高院的說法存有錯誤。判斷陳述書中,原審裁判法院亦大篇幅敘述和探討閉路影片和案中證人供詞及證據的關係。事實上,原審過程中,法官就閉路影片的內容,傳召了十多名證人,以求能全面掌握當時的情況,作出合乎事實的分析。
此外,原審裁判官曾指,梁振英所指的震驚,乃內心的感受,不一定會明顯表露出來。任何人聽到有玻璃爆裂聲,而聲響亦不在遠處發出時,也會感震驚。原審庭亦指,在梁振英見不到「掟」玻璃器皿的情形,而擔心有坐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況下再施襲,也擔心施襲者衝破防綫進行襲擊,是可以理解,加上水杯落地點與梁振英距離約1.5米,法庭認為屬「不遠處」,加上有可能濺起玻璃碎,判斷是會對梁振英構成潛在危險。
由此可見,原審法庭的判決乃基於事實的推斷,有考慮閉路影片、玻璃杯的落地點、梁振英當時的反應、以及其他環境證供。
推翻原審法理 欠缺穩妥理據
以上原審法庭的判決理由,具體且全面,卻在高等法院中於沒有指出裁判官的法理或事實錯誤下被指「不充分」而被推翻。但高院在明知沒有「耳聞目睹」證人作供的優勢時,單方面考慮閉路影片,而忽略了案件其他關鍵的環境證供,包括當時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身份,玻璃杯碎裂的地方乃離梁振英的不遠處等事實,筆者欲問,何以高院法官能得出如此判理比原審裁決更「充分」、更全面的結論?
梁振英有否因「掟」水杯而憂慮或震驚本是「主觀感受」,因此在推斷過程中應對當時梁振英的身份及現場環境予以考慮:固然,若以常人角度出發,受襲擊時或吵鬧,或叫嚎,本屬常理。作為香港決策者,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立法會議事廳上保持穩重鎮靜,所謂「處變不驚」,或英文稱之為“Self - imposed”,實在不應影響黃毓民施襲行為的理解。就算他沒有面露驚恐之情,也可以視作對暴力不低頭的表現,而並不代表心中對即時暴力毫無擔憂。
若以因梁振英沒有顯露特定表情或作出受嚇反應,而判斷其沒有因「掟」水杯感憂慮,是忽略了受害者當時的環境及身份因素。假若此案成「襲擊」罪的先例,更會增加控方的舉證責任,讓一些暴行因受害者沒有「適時」做出令法庭「滿意」的情緒表現,導致公義不彰,情況就像若性侵受害人沒有聲嘶力竭叫喊,施暴者因而不入罪,一樣荒謬。如此一來,犯罪行為將由本來法庭自主判斷案情是否犯法,變為受害者製造條件讓暴行符合罪案門檻。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法庭在判斷證人「主觀感受」時,其標準及拿捏本要考慮證人的狀況及環境,特別是當案件關鍵乃在於上述情感時,該審視準則更要嚴謹和貼近當事人。所以,在法庭上以第三者身份審視案件時,每項環境證供都變得非常重要。高等法院在沒有全盤了解這些事實去推斷梁振英的「主觀感受」,只依靠閉路影片作出有關推斷,實難令人信服。
黃毓民大動作「掟」杯 卻無犯罪意圖?
另一方面,法庭在犯罪意圖上的判決,同樣令人摸不著頭腦。
黃毓民於「掟」杯案中一直聲稱自己無意傷害任何人,旨在抗議、羞辱行政長官、或做成混亂而已。
原審法庭拒絕了黃毓民所指的「對事不對人」辯解,認為被告在庭上供詞指要羞辱行政長官,表示被告的抗議及針對對象則為梁振英,而不存在「不對人」的說法。原審法庭上黃毓民「掟」杯的手勢,包括有否涉及「向後拉」的動作,受主控仔細盤問,而原審法庭最終認為黃毓民乃迴避問題,不接納黃氏證供外,從黃毓民可從心決定怎樣處理那隻水杯,到「大動作」用力「掟」出水杯去看,認為被告是刻意「掟」出玻璃杯。此外,原審案中控方曾問黃毓民,在他被保安制止時,他大可選擇不「掟」杯,但黃毓民則回應道:「關你叉事,我係要抗爭」。從這裡能解釋到,原審法庭在判決時,何以指出黃毓民在所不計令梁振英憂慮受非法及即時武力侵犯。
但到了上訴案中,高院在沒有明確理由下接納黃毓民「對事不對人」的論述,同時將對黃氏當時動作而作的推斷一概排除。高等法院指,儘管黃毓民是蓄意「掟」出玻璃杯,但在考慮種種因素,包括其「對事不對人」的論述,及一貫行徑,即以往「掟」蕉,「搶」文件等等,因而認為「襲擊」梁振英的意圖不成立。
過往惡行 反成辯解
一般而言,在法理上以嫌疑人過往行逕作為判決理由,乃違反法治精神的舉措。事實上,在原審案中,裁判官就黃毓民過往「掟」物行為及被檢控的事件曾指,不會對那些資料予以考慮,並會將其剔除,不予比重。既是如此,何以高院會無故將這些事件放進判決理由中?再者,黃毓民在原審法庭上就過往行為有作解釋,他指「掟」衣服是為了「送衣服給領導人穿」,拍毀名牌、搶文件等暴行則全為「對事不對人」。如此狡辯,以簡單推理亦能得出黃氏乃為其赤裸的犯罪意圖作開脫,高院為何會信服以往的暴力行為不具針對人的目的?
法庭這裡的判詞,有如在鼓勵議會,甚至社會的持續暴力行徑。假設有一家庭,丈夫多年來都因家務問題作勢佯打來威嚇妻子,而到丈夫有一次當真動手,卻揮拳不中時,若按法庭是次道理,施暴丈夫乃「對家事非對人」,而考慮過往暴行都只流於形式而沒有實際傷害,是次揮拳亦理應不帶犯罪意圖。此般判理,難道不為縱惡?當以往惡行非但不成施暴者犯罪意圖的參考,更反成暴徒的辯解理由時,敢問法庭,如此案例,難道不會讓「惡者愈惡」嗎?
筆者尊重法庭,但是次判決,不得不教筆者失望,亦為受害者感不值。《基本法》所確立的普通法體制,保障商業社會,守護社會秩序,解決民生糾紛。多年來,香港的法治體制行之有效,其權威性一直受國際稱道。然而,如此判案,從筆者眼中來看,法院的地位正受挑戰,而挑戰者正是法院自身。
圖片來源:RT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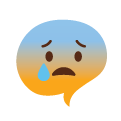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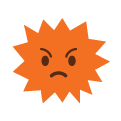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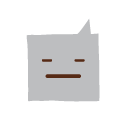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