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作:王應立,中文翻譯:黃啟樟
(七)軍部副官: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史迪威在1935年七月返回北京履職。至此他在軍隊已服務了三十一年,才被晉升至上校的官階。當時南京才是中國的首都,但史迪威卻被遣派到北京去填補軍部副官的空缺,理由安在?塔奇曼及他本人對這點都沒有作出任何解釋。史迪威負責情報工作,為陸軍部(War Department)搜集軍事及政治資料。他從中國官方及非官方的途徑入手,喜歡和當地學者,滿州過氣皇族成員及玉石商人接觸,而故意避開一些洋人俱樂部及北京會所的社交活動。
史迪威和其他洋人一樣,居住在四合院(quadrangle house)內,比得上廣州總督府一般豪華,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非一般華人所能擁有。四合院是由一個中心庭院及三個生活間組合而成的。這些建築物在今天的北京已成為富人的豪宅,售價往往在數百萬美元之上。洋人對北京的污濁與貧窮可以視而不見,因為他們遠離這些環境,享受優質及地位超越的生活,家務有家傭代勞,使他們感覺比留在老家更勝一籌。
塔奇曼對華人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與生俱來便賦有高貴的品質,自尊心重,富幽默感,耐力強,思維敏捷,中國女性外型優雅。”史迪威的助手巴雷特上尉(Captain Barrett),是洋人圈內的語言專家,對中國人更加讚不絕口:“他們聰明過人,講究文明,具有魅力,而且操縱自如;難得的是:他們的外表也非常吸引人。”塔奇曼及巴雷特對中國人謚美之言,使人相信他們圈子內的華人都屬於一些有教養的上流社會階級,和史迪威經常接觸的苦力,勞工及士兵的基層截然不同。由於所屬之社會層次不同,華人對衣著,衛生,談吐,儀態,知識及行為的要求分別很大,在當時的社會階級分明,一目了然。塔奇曼對華人亦有負面的批評:“缺乏誠信及忠心,沉溺於貪污舞弊,不可靠,傲慢自大,敏感過人。。。。。。”不過塔奇曼對《孫子兵法》評價很高,三千年前的理論仍可在今天採用,有助於解讀勞塞維茨(Clausewitz)的戰術,也能準確預測拿破崙(Napoleon)的軍事行動。這本書很精簡,已譯成多種文字,成為西點軍校及商科學院的教材。商場如戰場,孫子兵法極受重視。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塔奇曼毫不猶豫便引用了史迪威對中國人存有的偏見作為依據,誤判中國人是個缺乏誠信的民族。殊不知誠信及孝道是中國傳統教育的骨幹,並受到社會各階層的重視。這些道德準則也是孔子學說的金枝玉葉。不過忠心耿耿及誠實都不可簡單解釋,而且必須適當運用。在戰場上為了克敵致勝,必須使用詭計引誘敵人,偽造標誌誤導敵人,製造亂象蒙蔽敵人,散播謠言困擾敵人。這都是戰術上的謀略,何況兵不厭詐。
貪污在很多國家及社會都存在,並非中國人獨有的「專利權」,英國,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都同樣必須面對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沒有一個警察機關不存在貪污腐化的陋習。奧運會,國際足聯(FIFA),環球貿易,國防訂單等等,都存在不少誘發貪污的漏洞,防不勝防。曾經在中國流傳過一個有關貪污的笑話:在基督教傳教士來華之前,中國人懂得向誰賄賂,付出金錢之後便能把事情辦妥;但當傳教士來華之後,老百姓再不知向何方神聖賄賂,也不知道賄款多少才奏效,結果什麼事也沒有做到。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故事:傳教士過份熱心幫助中國人清除陋習,適得其反,善意造成惡果,原本的社會運作雖然不值得鼓勵,總好過一事無成。
在任何文化及族裔群中,社會都是由良民及惡漢組成的,良莠不齊。在美國幾乎每年都有各式各樣的選舉,巨額政治捐款從不同渠道送到每個候選人的手
里,支付競選費用。總統候選人必須籌集十億以上的資金才有希望問津總統寶座,參議院的候選人也必須籌備數千萬元的經費才可望成功,由此類推,權力與金錢是分不開的。有意競逐公共工程項目的商人便知道政治捐款或積極參與籌款活動是製造商機的捷徑,不善此道者或掌握不準這種禮儀的門外漢,在投標的過程中肯定被拒於門外。作者稱之為合法貪污!“先購票,才進場“(You want to play, you have to pay。)
由於國際聯盟(美國非成員國)之軟弱無能,日本的侵華行動節節升級,並按照他們定下的時間表及計劃推進。中國為了防止失去滿州和日本簽署了塘沽休戰協議(Tangku Truce),但兩年之後,即1935年,日本關東軍又強廹國民黨軍隊撤出屬於中國領土的河北省(Hebei Province)。蔣介石的最高副手何應欽(He Yingqin)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要求。
山東省軍閥韓復渠(Han Fuqu),曾與馮玉祥(Feng Yuxiang)結盟,拒絕蔣介石的軍隊越過他屬下的地盤,直到當時的總督宋哲元將軍(General Song Zheyuan)向日本求和及受到屈辱為止。蔣介石因為得不到西線後方的支援,唯有等待時機,靜觀其變。蔣介石的審慎態度被西方國家誤解為缺乏果斷,也被國人鄙視為懦夫的行為。這些貶義之詞便是當時的記者,政客,美國及西方國家民眾對蔣介石的觀感。他們認為向磚牆砸雞蛋猶勝於消極不動。史迪威及塔奇曼不斷攻擊蔣介石囤積兵力不抵抗日本的決定。其實蔣介石另有計劃,抗敵不可盲動,必須憑實力及掌握時機。蔣介石的審慎態度不但沒有獲得讚譽,並曾經受到譏諷是一個缺乏軍事才能只會玩弄政治手段的人物。
墨索里尼(Mussolini)在五月向埃塞俄比亞(Ethiopia)進攻,希特勒也準備在同一時間入侵萊茵蘭(Rhineland)。美國國會立即在1935年通過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防止美國向交戰國家售賣軍火,跟著在1936,37及39年依據同一理由定下三項新法令,禁止美國直接捲入境外戰爭及不准許總統委派顧問參與境外事務。
當時美國和西方國家只聚焦於歐洲發生的糾紛,完全忽略中國仍須向日本及歐洲八強繳納巨額的戰爭賠款:1895年發生的中日戰爭,中國戰敗,須向日本賠償九億兩白銀;1901年義和團觸發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中國節節敗退,屈辱求和,並須付出沉重的戰敗代價。至此日本已將滿州及長城以北的地區全面控制。
國民政府在1936年定都南京,要求外國使館從北平遷到那裡去,但很多國家都不願意將他們的高層外交人員南調。其中史迪威和美國軍方高層認為留在中國北方更有利於他們的任務。史迪威只出現於美國南京大使館的開幕典禮,隨即便搭乘美國海軍戰艦奧古斯塔號(USS Augusta)前往暹羅(Siam)訪問。他得到海軍部門的厚待,有點意想不到。史迪威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檢視暹羅軍隊之實況,然後作出報告。當任務完成後便返回北平。
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軍隊向西推進而一直沒有受阻,鼓勵日本軍國主義者加速他們的侵華計劃,在察哈爾(Chahar),綏遠(Suiyuan),山西(Shansai)及山東(Shantung)的邊境大量集結軍力。日本人打算扶植宋哲元將軍(General Sung Che-yuan)在北方成立對抗蔣介石的傀儡政權。中國內部的其他勢力,包括宋子文(T V Soong),胡適(Hu Hsih)和外交部要員都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失望。
塔奇曼形容國民黨的領導權沒落,沒法實現第二及第三階段之民生及民主的主張。政府向農民徵收四十四種不同稅項,仍感不足,再巧立名目增加稅收。永遠都是由老百姓(塔奇曼莫名其妙將它譯作Old Hundred Names)向政府進貢的。很明顯這樣直譯是錯誤的。其實美國的情況和中國差不多,都是由一成人口繳付九成的稅款。佔了中國人口九成的農民,生活在農村裡,收入極少,絕對沒有能力繳付如塔奇曼所說的四十四項課稅。中國的納稅人是由地主,商人,礦場老闆及企業家組成的。他們向政府繳稅。可惜大部分稅收都被政府用於戰爭賠償,非如塔奇曼指控蔣介石把它用來擴張他的軍隊。
日本在使用武力外侵的年代,國防經費佔了國家財政預算的75%,而這些支出很多是由中國賠款來填充。自從在美國投身工作之後,我每年都必須向聯邦政府繳納入息稅,也必須向加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繳付其他稅項。從最新統計,美國共有六十種不同名目的稅項向國民徵收。假若不信,可屈指一算,便知所說非假。眾所周知,一半的美國公民從來未繳過稅。有人或會為他們辯護:窮人亦須支付購物稅,路費及汽油稅等等。其實這些支出都是從政府每月的補貼中拿出,非窮人的工作酬勞。由此可見,塔奇曼借稅務為題發揮貶低中國人及蔣介石的言論是缺乏理據支持的。她刻意發表不利於對蔣介石的訊息。
對國民黨政府貪污無能......的指責不絕於耳。我們不妨也看美國援助中國的效率又是否恰如其分?這些留侍以後討論。
在很短的時間內河北的省長便經過五次更換,安徽的省長竟然也換了六次之多,他們猶如走馬燈地此起彼落。中國時局動蕩不安,人事更替頻仍。那美國又如何呢?想不到太平盛世的奧克蘭市(Oakland)在2016年的六月,警察局長在八天之內竟然也換了四次。
在1936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因推動社會改革新政策(New Deal socialist program)遭遇反對而陷入困境。在同一時間蔣介石也被西方報章猛烈評擊貪污無能。殊不知,中國政府各個部門,眾多企業,商業機構及個人正在不動聲色,重建以美國模式作為藍本的教育制度,成立合伙公司,修建鐵路及公路,改進農業生產,發展輕工業,生產消費品及在北方投資開拓重工業。雖然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及西方的惡意煽動與責難,中國的內部矛盾卻逐漸減少。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Johnson)曾表示對蔣介石失去信心,卻認為只有他才可團結中國。能說中文的他也曾一針見血地描繪中國已變成一團果醬一樣,任人踐踏。日本已取代英國成為中國毒品市場的最大供應商,並在滿州生產,保証貨品源源不絕。
從1911年至1941年美國政府一直沒有定下向中國援助的具體方案,因為華盛頓方面很少收聽到關於中國處於水深火熱需緊急向外求援的報導。為什麼會這樣呢?任誰也說不清楚。很明顯,英國和美國都不願他們自己被捲入到遠東的中日爭端中去。很多美國人都不能肯定:“對中國施以援手是否值得......如果中國人不能自救,我們實在不應對事件干預,避免激發起日本的敵意”。
在1935年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只佔外資總數的1%,中美之間的貿易也只佔總數的4%。以當時中國人口已達世界人口的五份之一為基礎,以上的經濟數據可說微不足道。當年中國非常貧窮,引不起美國和英國的重視。在同一時期日本積極宣揚及推動以日本為首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主張,目標類似十九世紀美國鼓吹以美國為中心的環球政䇿。
其實日本早在1935年之前的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時期已定下唯我獨尊的“昭昭天命”政策。日本目睹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以皇家海軍(Royal Navy)橫掃世界,將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亞,南非,加納(Ghana),塞拉利昂(Sierra Leone),黃金海岸(Gold Coast),尼日利亞(Nigeria),岡比亞(Gambia),肯尼亞(Kenya),鳥干達(Uganda),羅得西亞(Rhodesia/Zimbawe),埃及(Egypt),蘇丹(Sudan)及加勒比海(Caribbean)一些地區佔領,約佔全球土地面積的四份一以上,成為永遠不見落日的王國。
美國向拿破崙購入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之後,繼續添購德薩斯州(Texa);在1840至1841年與墨西哥發生戰爭,打敗墨西哥,佔領了新墨西哥州,亞里桑那州及加利福尼亞州;美國又向俄羅斯購入阿垃斯加;在1898年與西班牙戰爭,打敗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Puerto Rico),關島(Guam)及菲律賓。在1893年,夏威夷的白人居民向夏威夷王國的女王(Queen Liliuokalani)發動政變,將夏威夷移交美國政府接管。
日本是個島國,以英國為師,建立了在遠東地區最強大的海軍隊伍。她以武力侵犯鄰國,取得節節勝利。她在1895年打敗了幅員遼闊的中國,也在1905年戰勝了擁有先進設備的海軍及陸軍的沙皇俄國。
充滿朝氣的明治(Mejii)天皇死後將王位傳給兒子大正(Taisho),一個西化的花花公子,不久也死去,由裕仁天皇(Hirohito)在1926年12月25日接位,開始了昭和王朝。這是明治登位後的五十八年,也是他逝世後的十四年。明治對日本經濟及軍事西化的參與及貢獻直到今天仍受到爭論,雖然如此,日本維新運動在他統治期內發生是無庸置疑的。新成立的國會(diet)缺乏實際權力,國王也被擁有實權的官僚集團隔離。能夠在政壇上呼風喚雨的都是一小撮擁有兵權的政客及財閥。
在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版了兩本由美國作家撰寫的書,討論日本二十世紀的歷史,政治及軍事,也涉及明治,大正及裕仁皇朝期內發生的事蹟。其一是約翰托蘭(John Toland)所著的:《升起的太陽:衰落的日本帝國1936-1945(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由蘭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在1970年出版,並獲得1971年由普利策(Pulitzer Prize)頒發的“一般非小說類”創作大獎。他憑照日本人的觀點撰寫歷史,對日皇不參與戰爭決策的說法不表異議;其二是巴甘米尼(David Bergamini)在1971年發表的《日本帝國陰謀論(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詳細揭發裕仁天皇及其王室成員在戰爭時期曾直接參與政策的釐定及執行。兩個享譽世界的美國作家對日本歷史竟然會產生出如此截然不同的解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巴甘米尼的批評者曾質疑他取用的資料來源的可靠性。我們或許可比較兩個作者的背景,再加以分析。托蘭的妻子雖然是日本人,但他不諳日文。她負責為他翻譯日文的資料,及為他向日本退伍軍人訪問時擔任翻譯員。巴甘米尼在日本成長,精通日文,在戰爭時期曾被拘留在戰俘營內,直到戰爭結束。他的研究工作比較直接及不需假借他人。托蘭必須依據他人供給資料,雖然如此,美國批評人卻認為可信度較高。這實在匪夷所思,也不符合常理。
托蘭在1982年的另一大作:《恥辱:珍珠港事件及其餘波(Infamy:Pearl Harbour and its Aftermath)》,揭露羅斯福事前已知道日本的突襲,但眾多歷史學家指責此為無稽之談。羅斯福從1913年三月到1920年八月,一直在威爾遜總統政權內擔任海軍助理部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Navy),負責處理海軍部的日常操作。他在1932年被選為總統,任期由1933年三月開始,直到他在1945年四月逝世為止。從1933年至1941年十二月,羅斯福在華盛頓主政了八年。史迪威認為總統在這段時間內仍與海軍保持緊密聯繫,也積極參與世界事務,對海軍操作固然瞭若指掌,對國際政局的變幻也能掌握。如果他對日本突襲珍珠港一役事前一無所知,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日本主張中國北部各省脫離中央成為自治區,引起學生不滿,他們於是在1935年十二月九日走上北平街頭抗議。塔奇曼認為這次群眾行動將中國的命運扭曲了。其實參加示威的學生只有二千到三千人,其他城市對他們反應平淡,視為地方性事件,不足重視。這次行動也沒有迫使政府改變任何政策。
日本政壇分成兩派:“主力打擊北方”及“主力打擊南方”兩大陣營,爭持不下。蘇聯誘發日本主力軍向中國南方進攻,避免和他們在北方接觸。西方聯盟也盡量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但如果日軍繼續南侵,戰爭就難以避免了。
史迪威奉命為盟軍搜集情報,不斷往返廣州及兩廣地區。他從桂林(Kweilin)經水路到達梧州(Wuchow),途中曾參觀過一所軍校(黃埔?Whampoa?),繼續前往南京,在那裡遇見了李宗仁(Li Tsung-jen),再到漢口(Hankow),然後搭乘火車返回北平。史迪威那時雖然只有五十三歲,哪料到十年後便離開人間。史迪威呈交約翰遜(Johnson)的報告總是批評中國政府沒有作出迎戰日本的準備。除此之外,史迪威也利用日軍未來的進攻策略來貶低蔣介石部署軍隊的能力,但事實証明他預計失誤,一文不值。他對蔣介石的批評也不外乎是:“什麼也沒有準備好!“
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New Life Movement),督促國民改良個人的行為質素,被史迪威譏諷為瑣屑無聊,將人民的視線從日本侵略及民族危難轉移到其他地方去。據史迪威估計,在1936年受中央控制的軍隊共有一百三十萬人,受地方控制的軍隊共有三十六萬人,仍未包括非正規部隊在內。蔣介石僱用德國專家訓練他的軍隊,並採用德國裝備。這和蔣介石“什麼也沒有準備好“的批評豈非前後矛盾?史迪威的報告還有很多前言不搭後語的地方:“蔣介石的權力來源猶如歐洲中世紀的國王,由地方侯爵向他歸赴而獲得。“果真如此,他便不需借助一百三十萬大軍來支撐及擁兵自重了。史迪威的G-2報告有如此的論說:“中國當時仍沒有出現另一個具有影響力的領導人物......找不到替代者便是中國的弱點......也是獨裁統治的常態”。此說猶如把真與偽混在一起而談,自圓其說,殊不知獨裁者的身邊是不容許有第二者的存在的。
史迪威又重返南京幾次,遇見何應欽(Ho Ying-chin),向他搜集共產黨第四軍(Fourth Army)的資料,又和張學良(Chang Hsueh-liang)接觸,了解他帶領由滿州調動到西安(Sian)的東北部隊的情況。史迪威在中國四處奔波,對一切與日本有關的東西都有強烈的反感。筆者對史迪威給國民黨作出的軍力估計沒法肯定其正確性,塔奇曼對此亦不曾深入分析。史迪威雖然走遍中國大地,但罕有機會與各路軍閥接觸。他雖然把率領一百三十萬大軍的一百四十個將軍的名字都詳細記錄下來,但他是否也和這些人認識呢?令人懷疑。其實國民黨自己也沒有軍隊的準確人數。他們於2016年三月在互聯網上(ww2-weapons。com)公報的軍隊人數為一百七十萬人。史迪威的估計仍算接近。至於美國和日本其他方面列出的數據則為一百二十萬至二百五十萬人不等。
史迪威對中國產生的負面印象據說是由一個中國上校那裡得來的(他和上述的一百四十個將軍及眾多軍閥都有接觸,為什麼會偏向一個下級軍人套取資料的論述呢?)。“美國是能夠阻止日本侵略的,如果她將計劃付諸行動”,這句話猶如說:“中國人喜歡依賴他人出頭替他們幹些自己擔當不起的事”,是充滿貶義之詞。其實那個中國上校要表達的是:如果美國今天按兵不動,日本將會找上門來。結果不幸言中,日本突襲珍珠港便是按照這個預警而發生的。在隨後的戰役中,中國也向美國軍方及西方聯盟示範對抗日本取勝之道。
塔奇曼曾引用中國道教之格言“無為而無不為”來形容蔣介石的消極態度:“萬事不動也會自動化解!”“其實道教“無為”的含義是:如果我們對萬物一無所求,它們的重要性便會失去,但對一般人來說:“該做的事我們都必須做,不該做的事我們便不要做”。莎士比亞的大《哈姆雷特》中也有發人深思的問話:“是或不是,問題的重點便在這裡”。如塔奇曼能夠引用基督教的守則(Ecclesiastes 3:1):“世上萬事皆有其序,也會於適當的時間與空間發揮其作用”,這樣會比較貼近。蔣介石成為基督徒已超過八年,每天都背誦聖經。他受基督教的影響,不言而喻。
塔奇曼指出:除了蔣介石沒法抵抗日本入侵之外,墨索里尼輕易取得埃塞俄比亞(Ethiopia),希特勒直闖萊茵蘭(Rhineland),西方國家對這些公然侵略的行動也同樣愛莫能助。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唯一點起抗敵之火的力量,在山西向日本還擊。史迪威前往觀察,發現共產黨只和閻錫山的殘餘部隊在那邊發生零星的小衝突。他形容:“若將中國軍隊的具體表現來評估他們的作戰能力,可謂接近坐以待斃一般的低劣。”
過去史迪威曾高度評價閻錫山軍隊的質素,但如今才知道他們的表現如此不濟。其實史迪威不察實情:共軍和閻軍是不會在戰場上打個你死我活的,他們只是小試鋒芒便適可而止。共產黨也不會為抵抗日軍而賣命,他們行動的目的在於尋求軍備及糧餉的補充。英國人對史迪威搜集共產黨情報的能力有高度評價。至於他是從什麼途徑取得這些資訊他也沒有清楚交代。
塔奇曼從史迪威及眾多美國人的口中聽到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都是肯定的:“暴政引發反抗,代價沉重......饑荒頻仍,地主無處不在,沉重的租金,土地所有權的重新分配等等措施,鼓動人民紛紛投入共產黨的陣營,但中國人與生俱來並非傾向共產主義的。很多西方人對此有同感。在1936年十一月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發表他的作品«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向世界表揚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的英勇事蹟,言之鑿鑿。很多外國記者向著延安(Yan'an)蜂擁而至,接受同樣的愚弄。毛澤東當時只偽裝與國民黨攜手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蔣介石在1936年十二月前往西安(Sian),策劃第六次剿共行動。他委任張學良領導當時駐守西安的部隊。張與周恩來早已秘密接觸,尋求合作。當蔣介石到達時,張和陝西(Shaanxi)的楊虎城(Yang Hucheng)及其他國民黨將領密謀將他綁架。蔣介石的命運在未來的十四天便完全由這班叛徒主宰。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裡曾表示願意為國犧牲,義不容辭。雖然有些派別主張把蔣處死,但張學良和共產黨人都不願負起社會因此發生動亂的責任。蘇聯政府也不同意處死蔣介石的決定。莫斯科方面預見中國缺乏替代蔣介石的人物,失控的局面只會對日本有利,必須盡量避免。西方列強也擔心局勢混亂。蔣介石的囚禁終於在各方憂心忡忡之下,由蔣夫人親赴西安營救丈夫得到圓滿解決。蔣夫人的出現顯示萬眾一心。她也取得曾經在黃埔軍校擔任教職的周恩來的支持,同意國共合作,由蔣介石率領雙方合併的軍隊向日本宣戰。
史迪威對國共和解協議抱著懷疑的態度,認為政府表面積極備戰,實在利用拖延之計,將問題交由他人代為解決。中國嚴重缺乏資源,只能向外求助才可望解決困難。和日本比較,中國的資產只是“某些空洞的數字,數不盡的仇恨及遼闊但荒廢的土地。她既缺乏領導人,道德敗壞,一盤散沙,軍火陳舊過時,軍隊都是烏合之眾。”
史迪威誇稱自己曾熟讀清朝名將左宗棠(Zuo Zongtang)平息1870年回教徒叛亂所使用的戰術。他說:“左將軍能掌握形勢,善於用兵,速戰速決。他能當機立斷,無所不能,令其他名氣比他更盛的領導者也感到困惑。這次軍事創舉,英勇敢善戰的士兵固然功不可沒,英明的指揮官更是居功厥偉。(歷史學家罕有之讚美之詞)“塔奇曼所指的戰役便是發生在1862-1877年清朝同治(Tongzhi)皇帝時期之同治回變(Hui Minority War),一場曠日持久的少數民族叛亂,受影響的地區包括陝西(Shaanxi),甘肅(Gansu),寧夏(Ningxia)及新疆省(Xinjiang)。塔奇曼沒有將這段歷史的過程詳細描述,史迪威也沒有說明他獲取這些資料的來源。這是一連串非常複雜及毫無明確目標的事件,英國劍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80年曾對此作出比較具有學術性的的論述。一些比他較早的記載也曾在中文及英文的文獻中出現,但在塔奇曼的參考目錄中卻隻字不提。其實左宗棠聲名大噪是在他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之後才開始的,反映他對國家的貢獻。史迪威和塔奇曼對左宗棠的讚頌只不過是他們兩人的憑空想像罷了。
左宗棠在戰場上取得勝利除了主觀條件優越之外,叛軍往往一經接觸便投降,立即歸赴皇軍。他率領的軍隊在進入新疆時,完全沒有受到反抗,猶如進入無人之境。當年也曾發生過屠殺的事件,約有二千萬平民死於非命。這些死亡都不是由戰鬥引起的。這情況與太平天國叛亂的年代相似,老百姓遭受饑荒,流離失所,及敵對雙方的殺戮。如果史迪威認為這些歷史事件對他在中國的任務有著指導性的啟發,我們不免要問:他到底如何解讀歷史及從中獲益。不管怎麼說,史迪威仍感到中國時局黑暗,打算到睢陽(Suiyang)及蒙古去,也希望到五台山(Wutai Shan)一看,並從那裡徒步走向150英里以外的鐵路。其實此段路程不足100英里,他的估計又再次出錯了。
史迪威的聲名逐漸冒起,再經林奇上校(Colonel Lynch)返回華盛頓後為他吹噓,成為“最熟識中國及遠東的軍官,他走遍中國取得的經驗超越任何人”。殊不知“一知半解是件危險的事”,非戒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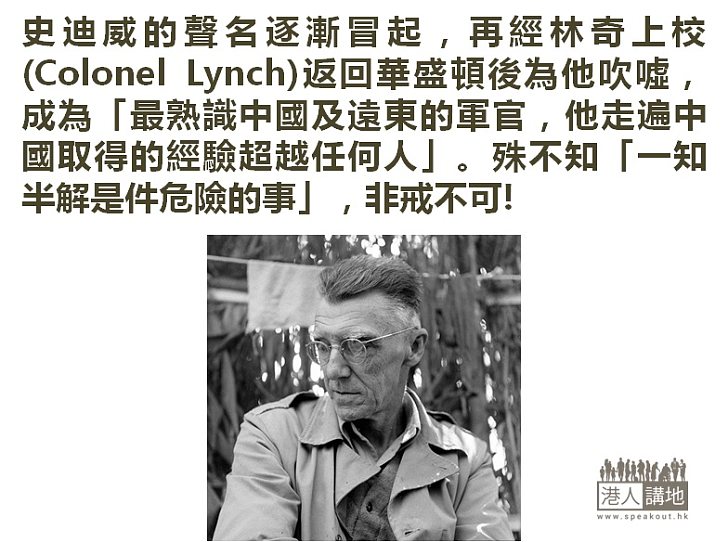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