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作:王應立,中文翻譯:黃啟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大量減少陸軍人數,史迪威感覺未來升級的機會將會微乎其微,因而失去了耐性。他得到一個在國防情報部門(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服務的朋友推薦,前往中國出任軍方的外語代表。塔奇曼對哈丁(Harding)在總統選舉獲勝所下的評論是:「哈丁善用威爾遜對待中國犯下的錯失作為攻擊現任總統政績的武器,將競選對手打敗」。但真正原因並非如她所指,而且事實也勝於雄辯。哈丁在1920年的總統大選中,以60比40之相差比數將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考克斯(James Cox)擊敗。支持他的選民包括德裔及愛爾蘭裔人和初次獲得選舉資格的女性選民。塔奇曼認為中國並非一項受到1920年選民關注的問題。當時民主黨共有十七人競逐總統提名。無獨有偶,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共和黨也有十七人競逐總統提名。當年和今天一樣,美國自由派傳媒均表示過多人競逐提名只會令選民眼花撩亂,難以選擇。當威爾遜健康發生問題及他主張的國際聯盟被參議院否決之後,民主黨的競選團隊立即亂了陣腳,潰不成軍。這樣看來,哈丁的勝利實在非由中國因素促成的。
史迪威及他的同僚因職務所需必須接受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辦的中文培訓課程。但經過一個月之後,他認為課程欠缺實用價值,課餘也缺乏中文對話的對象,便決定離開。史迪威曾被形容為一個優於發掘資源的人,筆者對此說法實在難以置信。眾所周知在伯克利附近有成千上萬的華裔居民,隨時隨地都可找到能說中文的對象。這些華人遍佈於洗衣店,菜市場,餐廳,雜貨店及各行各業中,隨處可見。
塔奇曼曾扯到中文的話題裡去,簡單介紹了中文的特性。筆者未能肯定塔奇曼曾否學過中文,認為她的觀點可能只是反映別人的意見。這些觀點大部分可接受,但塔奇曼半點沒有提過中文的文法,更未能指出中文比其他文字易學是基於文法簡單易懂。中文表達時間不須將動詞改變成不同時態,形容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是用同樣的字。中文動詞「吃」只有一個時態,沒有「eat, ate, eaten 或 eating」。中文名詞也沒有單數和複數之分。「牛」不須由「ox改成oxen」,「鼠」也不須由「mouse 變成 mice」。中文的代名詞也十分簡單,沒有主格,受格,所有格和賓格之分:如「I, me, mine, my, me」。中文名詞亦不分陽性,陰性及中性(英文和中文在這方面很相似,但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文字則仍墨守成規,一成不變)。除此之外,中文比其他語文也比較靈活,非依賴字母組合而成,而由部首合併出來,含義廣泛,變化多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水,草,樹木,人類,石頭等等。部首的含義容易掌握,縱使字體筆劃繁多或看來十分複雜,都離不開那些部首。書寫中文一般是由左至右及由上至下的,順序排列。中文是由象形文字演變出來,可望形生義,一目了然,無須經過拼音,既靈活又富效率性。不妨看看飛機艙內的安全告示,我們會發現中文最簡短而表達的意思和其他文字卻完全一樣。中文字句可從右至左寫,或左至右,也可從上至下,只有日文模仿了這個方式,其他語文便沒有這麼靈活了。韓文原本也利用中文的格式,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便改用語音法創造出來的字母去取代中文。
史迪威和妻子在1920年九月十八日抵達中國之後,搭乘火車前往北京。他花了十天的時間一面找房子一面到處遊玩。塔奇曼向讀者簡單介紹一下當時仍未對外國人開放的紫禁城。外國使館均設在北京靠近紫禁城那邊,明代及清代皇朝的皇宮及衙門均設於紫禁城內。在史迪威到達之前,中國已由不同派系的軍閥割據。真系與皖系在1922年七月發生衝突,真系由曹錕領導,得到吳佩孚的支持,將皖系打敗,其首領段祺瑞失敗後逃入日本管轄的天津。到1922年六月,由吳佩孚領導的真系將奉天系的張作霖打敗,張慌忙逃向中國東北的滿州。中國南方由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管轄。英國和美國只承認控制北京的北洋政權。在1924年九月八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吳佩孚的肖像出現在它的封面上。塔奇曼竟然稱讚吳氏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中國人。吳實為北京保定軍校的畢業生,曾服務於袁世凱統領清政府的新軍。袁氏死後,他投向真系的地方勢力集團。在皖系及奉天系被真系打敗後,吳佩孚奉命再向奉天系宣戰。吳氏在北京遭遇到詭計多端及外號被稱為「玉帥」同黨馮玉祥的反叛,他的軍隊因此亂了陣腳,終於成為張作霖的手下敗將。張在早年只不過是一名土匪,打家劫舍,並曾以僱傭方式參與日俄戰爭。張也是一個草包子,但思想敏捷,受到地方權勢及財經界的支持,最終成為舉足輕重的地方軍閥,控制了整個滿州。塔奇曼對當時中國北方的三大軍閥:馮玉祥,張作霖及吳佩孚曾作出過簡單的描述。她對馮玉祥的印象是:一個彪形大漢,曾在時代雜誌封面出現過,戰後竟以學者身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並趁機探望史迪威的遺孀。塔奇曼反映史迪威對中國軍閥的印象說:「軍隊作戰能力不高。。。。。。發射大炮時十分輕率(這和大戰時的盟軍可謂不相伯仲!)。」
孫中山先生曾向西方國家尋求協助以鞏固他的領導地位,但只得到冷淡的回應。他於是轉向蘇聯求助並獲得支持。蘇聯答應伸出援手,使國民黨可以早日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因此可加入國民黨的組織,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由於缺乏武裝力量作後盾,舉步維艱。
史迪威到北京出任外語代表的任期是四年,同時可接受中文實習培訓。長居中國的洋人都喜歡有個中文名,史迪威這個中文名便是如此創造出來的。塔奇曼對它還加上潤飾,猶如一些好萊塢名星的中文譯名,使中國人可依照音韻,朗朗上口。史迪威只接受了半年的中文培訓,便到國際紅十字會的救災單位工作,協助建造通往山西的路,在施工的四個月裡能夠與中國的老百姓實地接觸及觀察他們的生活情況。史迪威一貫缺乏在某處久留的耐心,塔奇曼卻將他與格闌特總統(Ulysses S。 Grant)比較,不知憑什麼來說?築路工程被擱置,藉口是:「中國政府對救災計劃不投入,緊急的糧食運輸往往受到阻延,因此未能及時解除饑荒危機,造成大量死亡。」根據塔奇曼之記載:「1920年的饑荒是四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大小饑荒每年都在中國各地發生,雖然如此,塔奇曼所記載的1920年大饑荒卻在世界史紀錄中從未出現過。發生在俄國的1921年大饑荒死了五百萬人,在1924至1925年期間在俄國又出現了另一次大饑荒,在1928-1929年非洲的盧旺達布隆迪(Ruwanda-Burundi)也發生了一次大饑荒,在1928-1930年中國北方又出現另一次大饑荒。塔奇曼所提到的那條由史迪威協助興建的道路,是為了將餘糧輸送到西北饑饉地區去,但根據史實西北各省從沒有出現過饑荒。無庸置疑,為期僅四個月的築路工程所產生之成效是非常有限的,何必誇大其貢獻呢?二十世紀在中國發生最嚴重的饑荒是1959-1961年的那一次,死亡人數估計有一千五百萬到四千三百萬,是由於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失誤導致。任何對中國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中國每個朝代的政府都一直有儲糧賑災的計劃,可緩解民困。這些計劃或有不足之處,但它們一直存在以備不時之需。西方認為中國面對災難時缺乏應變能力是沒有理據的。塔奇曼曾引述美國威爾遜總統的話:「中國人過分依賴美國人的智慧與領導。」筆者大膽的說:果真如此,中國人將會一無所得。更使人難以置信的是:「傳教士推動的救災運動引發起源源不絕的捐款,使築路計劃能夠如期完成。」這些報導卻找不出任何証據去支持。在抗日戰爭那段日子裡,美國支助中國的捐款可謂微不足道,他們只象徵性地將零錢投入安放在中餐館的捐款小箱便算。大部分捐款都是來自海外華僑及美籍華人。塔奇曼和史迪威同樣感到傳教士曾將中國發生的饑荒誇大,藉此搜集更多捐款。那是怎麼回事?傳教士豈非利用欺騙手段去斂財?
史迪威負責的築路計劃是將黃河流域的方山(Fenchow)及軍渡(Jung-tu)連接起來,全程約82英里。建築規格對路面闊度(22英尺),材料等級都有明確規定,計劃必須在1921年八月一日(塔奇曼漏寫了年份)前完成。他手下共有十二名外國助理,其中一個是來自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土木工程師。當時山西省是閻錫山的勢力範圍,他享有「模範總督」的美譽,施行開明進步的政策,對老百姓及部下關懷備致。史迪威負責領導六千工人,指揮中國測量人員進行探測的工作,協助工程師分工合作,組織工隊,挑選材料,決定施工程序,同時也可學習山西方言。幸好能說國語(普通話)的人有很多,方便溝通。塔奇曼對這些情況的描述卻有不少疑點,與事實不符。山西省的面積很小,闊度僅有180英里,一條82英里長的公路幾乎橫跨了該省版圖的一半。山西的山脈及河流都是從北向南伸展的,河流的東西兩岸都是崇山峻嶺,公路及鐵路都必須順著山勢由北向南走。她列舉的城鎮都沒法在現代或過去的地圖上找出來。山西人縱使能說國語,他們濃厚的山西口音也會令到精通國語的人感到困難,更何況一些老外。
史迪威曾為閻錫山寫了一篇專欄並在(Infantry Journal)「步兵專刊」公開發表。他形容閻氏是一個開明的革新者,遠離權力鬥爭,專注於醫療服務及社會福利,為老百姓謀幸福。1920出版的時代雜誌在封面登上了閻的肖像,並在註腳加上了"中國未來總統"的讚美之詞。他後來參加抗日戰爭,頑抗敵軍,和他日本軍校的同窗在戰場上交手。
史迪威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山明水秀的滹沱河(Yu Tao-Ho?)天然峽谷度假地區。返回北京後,立即安排家人先搭乘火車再轉乘汽車,決心將家庭遷到那個世外桃源去。他將築路計劃交由某助理接管,提前退休,開始過其安逸的生活,閒來和家人打網球,到郊外野餐,為雜誌撰寫文章。無可置疑,史迪威是根本無意完成他的築路計劃的,只有塔奇曼才會認為他對那項任務由始至終都充滿熱忱。其實史迪威嚮往的只是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及他們所過的舒適生活。繼此之後,築路計劃再沒有被提起過,到底完工與否也無法可知。史迪威對中國人的描述只限於他圈子內接觸到的人。他對外交人員在北京的生活也感到心滿意足,只喜歡和妻子跳舞,沒有興趣與其他武官打橋牌或馬球。過了十一年(1932)之後,史迪威一個新聞記者朋友格特(John Goette)曾將當時的剪報寄給他,對山西築路計劃作了如下的報導:「那條公路現在已完全失去蹤影,是由於中國人習慣地懶於維修設施所致。」這又是另一次對中國人的惡意批評。但今天任何人只要到中國走一回,都會驚嘆中國人築路之驚人速度及他們那些超級公路之質量。回顧當年,美國和中國交通設施之落後大同小異。美國的主要公路會得到按時維修,其他小路則經年失修,凹凸不平,塵土飛揚。厚此薄彼的批評,實無必要。
根據塔奇曼的記載,山西的芳鄰陝西省(Shaanxi而非塔奇曼習慣使用的譯名Shensi,使它與Shansi容易混淆)的軍閥馮玉祥曾計劃聘請史迪威為他建設公路,將潼關(Tung Kuan)及西安(Xian)連接起來。馮氏本來屬於真系(Zhili Clique),但背叛了他的同系吳佩孚,奪取北京為據點並與國民黨聯盟起來。史迪威從北京搭乘火車往西安走,在離開終點前的一百英里轉乘馬車在破舊的小路繼續旅程,沿途都是人頭湧湧的群眾。遇到崎嶇不平的路段,他寧願安步當車。在路上他曾投宿於一些骯髒的小旅社,睡在佈滿跳蚤的臥床上。他目睹一些苦力花掉每天用勞力賺取得來的百份之三十金錢在鴉片上,質疑那些軍閥頭子為何不下令禁毒:「將鴉片燒燬,將販毒者繩之於法。」從史迪威的印象可見得他沒有熟讀中國的歷史,對林則徐禁煙引發之鴉片戰爭一無所知。英國及美國商人首先將鴉片強行輸入中國,日本在1895年中日戰爭將中國打敗後,佔據了中國東北的滿州,在那裡大量生產鴉片,並在中國市場推銷。塔奇曼未經思考便說:「中國的窮人吸食鴉片以抵抗饑餓的痛苦。其實,他們可將購買鴉片的錢花在食物上。」殊不知,當毒癮發作時,他們都必須吸進鴉片去解毒。眾所周知,美國每年因過量吸食毒品而死亡的便超過三萬人。美國毒品管制局(DEF)和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聯手禁毒每年耗費數萬億元,但成效卻差強人意。美國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一個毒梟被擒之後但另一個便立即可填上他的空缺,成千上萬噸的毒品仍源源不絕進入美國市場。塔奇曼對此視若無睹,卻將矛頭指向中國,而且大做文章!
塔奇曼在她的書內曾記述美國在1921-22年倡議的華盛頓海軍會議(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of 1921-22)的目標是限制軍備擴張,鼓勵中日談判解決爭端。「山東的存亡有賴於美國的正義良知!」美國民主黨認為共和黨善用這個吸引選票的口號使哈丁總統(President Harding)登上美國元首的寶座。其實此乃言過其實,華盛頓會議亦非為終止中日爭端而召開。美,英,日,法和義大利等五個國家利用華盛頓海軍會議,簽署了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ton Navy Treaty),限制他們的海軍艦隻數量比例控制在5:5:3:1:7之內。在同一會議上,美國,比利時,英國,中國,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葡萄牙公開確認中國的主權及保障其領土完整,簽署了「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並以一紙為憑證。這份九個國家簽署的文件卻完全缺乏執行的條款。當日本在1931年違反了協議時,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沒有一個願意站出來為中國主持公道。日本在1936年又故態復萌,違反了這個條約。眾所周知,英國和美國邀請中國參加會議的目的是利用她作借口以限制日本海軍實力的擴張。會議期間,專家們只顧計算艦隻的排水量,戰艦,巡洋艦及航空母艦的數量,艦上炮火的威力等等,將中國維護主權的議程完全忽視了。塔奇曼沒有對此加以批評,反而讚揚這份九國協議是華盛頓海軍會議的堅實成果(crown of the conference)。這項協議終於被1937年發生在上海的一場戰役徹底撕破,除了蔣介石曾經誠心誠意遵守之外,日本及所有盟友均把它當成廢紙一張。在此之前這項條約曾被呈上美國參議院討論,議院諸公明知它完全是假情假義及毫無約束力的一張廢紙,卻大義凜然地以66票對0票通過,表達保護中國主權的道義決心。美國這樣做一方面可洗滌對山東犯下的錯失,一方面可免除出兵的責任,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日本在這場智力競賽中讓英美佔了上風,除了將本身的實力洩漏之外並須接受由對方擬定的軍艦數量比例。殊不知英美兩國過分天真,誤信日本會遵守承諾,不會越雷池半步。華盛頓海軍會議之後,美國在1924年通過了「排日法案」(Japanese Exclusion Act),比在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遲了四十二年,設置障礙以限制華人和日本人歸化美籍。此等立法完全違反正義的精神。美國白種人對亞裔尤其是中國人的歧視一直延續很久。美國推行的「門戶開放」(Open Door)政策,旨在維護她與西方國家的權益,可瓜分弱勢中國的資源。
史迪威被遣送到奉天(Mukden)擔任工作,即今天之沈陽(Shenyang), 是滿州人對它的稱號。奉天是當年日本關東軍(Japanese Kwantung)在滿州地區的大本營。上任前他曾經到過日本並停留了七天,也到過蘇聯的海參威(Vladivostok)和朝鮮半島(Korea)一次。塔奇曼這樣記錄史迪威對日本留下的印象:「他們模仿德國人卻不倫不類,有形無實!但對國家忠心,具有組織能力,勇敢,有藝術修養,卻容易頭腦發熱及愚昧無知。」他在1923年又以外語幹事(foreign language officer)身分重遊日本兩次。史迪威也到過浙江,江西及湖南遊覽。他目睹的是:「鴉片貿易泛濫,受到地方勢力(督軍Tuchun)的保護,情況與日本截然不同,那裡吸食鴉片仍未普遍。」史迪威必然忽略了英國人及美國人在中國大力推銷鴉片的惡行,日本卻幸運地能逃此一劫。在1923年六月,史迪威到了外蒙古(Outer Mongolia)遊歷。他由長城張家口(Kalgan)的火車站搭乘汽車出發,花了三天時間,走了650英里,到達首都庫倫(Urga)。這是一個疑點重重及令人難以置信的旅程。從地圖可看到張家口(Jiangjiakou,比Kalgan普遍使用的譯名)那裡有個火車站。火車路線是先往西南方向走,經過大同(Datung)再朝北直達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Ulaanbaatar)。當年的外蒙仍屬中國的領土,地圖上沒有Urga這個地方,只能猜想它是Ulaanbaatar 的舊譯名。以前的記述說史迪威在山西坐木頭車(cart)要花上十八天才能完成一百英里路。如今他卻可在多屬沙漠地帶的外蒙古經年失修的道路上,只花三天時間便走完650英里。他從哪裡得到汽車作為交通工具?何方神聖為他安排行程呢?塔奇曼對這些疑問一律奉欠。更難以置信的是:史迪威居然能夠在踏上外蒙古征途之後的三十天從容攜眷返回美國。這些壯舉都在是他慶祝四十歲生辰之前完成的。
塔奇曼在她著作的第四章裡又錯誤地記述史迪威以外語幹事身分在北京花了四年學習中文,其實他在課堂逗留的時間少過八個月。在此期間他曾被委派到山西負責建造計劃中全長82英里的公路,之後又接受另一地方軍閥的要求前往陝西(Shaanxi)築路,但工程仍未啟動便因軍閥內鬥而擱置。史迪威除了和家人在北京閒度日子之外,也到過滿州地區,朝鮮,日本,中國中部三個省旅遊,而且在外蒙古逗留了一個月。他在旅途中結識了三個督軍首領(軍閥頭目):吳佩孚(Wu Peifu),馮玉祥(Feng Yuxiang)和閻錫山(Yan Xishan)。三人都在美國的時代雜誌(TIME)封面上出現過,為世人所知。史迪威讚揚閻錫山為「模範總督」,馮玉祥為「基督將軍」,吳佩孚為「謀略軍師」。無庸置疑,史迪威經過四年時間與這些人交往,或多或少都會掌握到一些中國人的特性。他除了獨自到各處遊歷之外,史迪威與家人一直留在北京,過著外交人員享有特權的生活,起居飲食有眾多家傭的照顧,閒暇時參加數不盡的茶聚及酒會作為社交活動,遠離平民百姓的生活圈子。縱使在參與築路那段日子裡,他和築路工人及士兵曾經生活在一起,但亦受到外賓的禮待與尊重。至於那三個曾經顯赫一時的軍閥,其光芒亦如曇花一現,最終被時間淹沒。在他們權力高峰時,中國只有三份之一的國土落在他們手下,其餘東,南及西部則由另外五十多個派系的地方勢力盤踞。若說史迪威和塔奇曼對中國有全盤性的了解實在會令人質疑。
在那個四分五裂的年代中國到底有多少個軍閥呢?我曾經指出這些地方勢力並非如塔奇曼統稱為「督軍」(Tuchun),他們都是軍閥。1911年10月11日在武漢(Wuhan)發生軍事暴動之後,全國各地同時發生了區域性的權力鬥爭,地方首領在靠近他們勢力範內擁兵自重,形成群雄割據的局面。清朝政權崩潰,到處出現了權力真空,前朝之軍政領袖趁機而起,填補這些漏洞,袁世凱(Yuen Shi-kai)便是其中之一。為使讀者對軍閥割據時代有個較清楚的地理輪廓,以下是一些影響力較大的軍閥及他們控制的地域,但遺漏仍在所難免。
(一)皖系(Anhui Clique):段祺瑞(Duan Qirui),除樹錚(Xu Shuxiang),盧永祥(Lu Yongxiang),倪嗣沖(Ni Sichong),曲同豐(Qu Tongfeng),吳光新(Wu Guangxin)
(二)直系(Zhili clique):馮國璋(Feng Guozhang),曹錕(Cao Kun),吳佩孚(Wu Peifu),孫傳芳(Sun Chuanfang),陸建章(Lu Jianzhang),馮玉祥(Feng Yuxiang)
(三)奉系(Feng clique):張作霖(Zhang Zuolin),張學良(Zhang Xueliang),張宗昌(Zhang Zongchang),萬福麟(Wan Fulin),郭松齡(Guo Songling),湯玉麟(Tang Yulin)
(四)國民軍(Guominjun):馮玉祥(前直系),胡㬌翼(Hu Jingyi),孫岳(Sun Yue)
(五)馬家軍(Ma clique):馬麒(Ma Qi, Qinghai),馬麟(Ma Lin),馬步芳(Ma Bufang),馬步青(Ma Buqing)
(六)新疆系(Xinjiang clique):楊增新(Yang Zengxin),馬福興(Ma Fuxing),馬紹武(Ma Shaowu),金樹仁(Jin Shuren)
(七)山東(Shandong):劉珍年(Liu Zhennian),韓復渠(Han Fuqu)
(八)寧夏(Ningxia Ma clique):馬鴻賓(Ma Hongbin),馬鴻逵(Ma Hongkui)
(九)陝西(Shaanxi):井岳季(Jing Yuexiu),楊虎城(Yang Hucheng)
(十)熱河(Rehe):湯五麟(Tang Yulin, Fengtien),孫殿英(Sun Dianying)
(十一)甘肅(Gansu Ma clique):馬仲英(Ma Zhongying),馬虎山(Ma Hushan)
(十二)河北(Hebei):宋哲元(Song Zheyuan)
(十三)河南(Henan):別廷芳(Bei Tingfang)
(十四)隋陽(Suiyuan):傅作義(Fu Zuoyi)
(十五)湖北(Hubei):王占元(Wang Zhangyuan)
(十六)湖南(Hunan):譚延闔(Tan Yankai),唐生智(Tang Shengzhi)
(十七)貴州(Guizhou):劉顯世(Liu Xianshi),王家烈(wang Jialie)
(十八)福建(Fujian):蔡廷鍇(Cai Tingkai),蔣光鼐(Jiang Guangnai)
(十九)雲南滇系(Yunnan):蔡鍔(Cai E),龍雲(Lung Yun),唐繼堯(Tang Jiyao)
(二十)四川,川系(Sichuan):劉湘(Liu Xiang),楊森(Yang Sen),鄧鍚侯(Deng Xihou)
(二十一)廣東(Guangdong):陳炯明(Chen Jiongming),陳濟棠(Chen Jitang),張發奎(Zhang Fakui)
(二十二)山西(Shansi):閻錫山(Yan Xishan)
(二十三)江西(Jiangxi):魯滌平(Lu Diping)
(二十四)浙江(Sichuan/Xikang):劉文輝(Liu Wenhui)
(二十五)桂系(Old Guangxi clique):陸榮延(Lu Rongting),林虎(Lin Hu),陳炳焜(Chen Binghun)
(二十六)新桂系(New Guangxi clique):李宗仁(Li Zongren),黃紹䇊(Huang Shaoxiong),白崇禧(Bai Chongxi)
(二十七)國民黨(Kuomintang KMT):孫逸仙(Sun Yatsen),蔣介石(Chiang Kai Shek, CKS),胡漢民(Hu Hanmin),廖仲凱(Liao Zhongkai),何應欽(He Yingqin),汪精衛(Wang Jingwei)
(二十八)共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毛澤東(Mao Zedong),周恩來(Zhou Enlai),朱德(Zhu De),彭德懷(Peng Dehuai),鄧小平(Deng Xiaoping),林彪(Lin Biao)
中國在軍閥割據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擁有的軍隊與土地非常有限。以延安(Yan'an)為根據地的共產黨只控制了5%之國土;實力集在中國南方的國民黨也只控制不到20%的土地。從上列圖表可知道中國的大片土地是落在眾多軍閥或其他地方勢力的手下。他們擁兵自重,徵收課稅,自行訓練軍隊。由此觀之,塔奇曼,史迪威,美國及西方國家不停指責蔣介石無能管治國家是基於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當時的蘇維埃聯邦(Soviet Union)由斯大林(Stalin)統治。他是個獨裁者,將所有反對者拘捕,勞改,謀殺,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斯大林獨攬大權,控制全局。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由四次連任的羅斯福總統(FDR)主政,他沒有面對軍閥割據的壓力,一直至1941年的十二月為止,始終國泰民安。大西洋那一邊的英國在1939年之前,也一直保持和平,同時享有豐富的資源及人才,可作為日後作戰的本錢。臨近中國的日本,由單一民族組成,長治久安,並可利用中國戰敗的巨額賠款擴展軍事力量。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領導人孫逸仙突然病逝,由蔣介石繼承,他以微不足道的資源,負起團結面對貧窮,流離失所,內憂外患的民眾的大任。試問當面對同一困境時,史迪威將能擔此重任嗎?換成丘吉爾,或羅斯福,甚至斯大林,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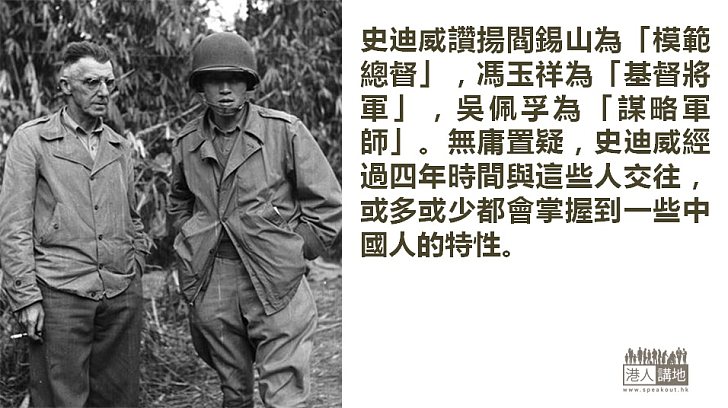

















評論